 成都4月17日消息,“我們也在等消息,唯一獲得的消息是律師告訴我們警方給孩子做了一次精神鑒定,但結(jié)果可能要月底、下月初才出來(lái)。”中國(guó)青年報(bào)記者4月17日聯(lián)系到川師殺人案嫌疑人滕某的母親,“我們不知道怎么表達(dá)我們的歉意。”她在電話那頭泣不成聲。
成都4月17日消息,“我們也在等消息,唯一獲得的消息是律師告訴我們警方給孩子做了一次精神鑒定,但結(jié)果可能要月底、下月初才出來(lái)。”中國(guó)青年報(bào)記者4月17日聯(lián)系到川師殺人案嫌疑人滕某的母親,“我們不知道怎么表達(dá)我們的歉意。”她在電話那頭泣不成聲。滕母稱家里人對(duì)“到底發(fā)生了什么事”一無(wú)所知,只知道滕某剛上大一時(shí)跟她抱怨過(guò)剛住宿舍不太適應(yīng),說(shuō)“宿舍晚上睡覺(jué)吵死了,放屁打呼嚕的,聲音太大影響睡覺(jué)。”滕母開導(dǎo)他要習(xí)慣,跟同學(xué)好好相處,“他比較愛干凈,睡眠不好,說(shuō)后來(lái)習(xí)慣些了。”
這不是滕某給家人帶來(lái)的第一次意外。據(jù)滕母描述,滕某在中學(xué)時(shí)曾兩次割腕自殺,第二次險(xiǎn)些未能搶救成功,“在醫(yī)院住了半個(gè)多月”,之后轉(zhuǎn)學(xué)。
滕母回憶,滕某從小調(diào)皮外向,但到了初中突然變得內(nèi)向。讀初一那年的某晚,一家人本來(lái)一起看電視說(shuō)笑,半夜滕某被發(fā)現(xiàn)在屋里用水果刀割腕,家人送去醫(yī)院搶救縫針、住院。“之后問(wèn)他什么情況,他說(shuō)不清楚,自己也不知道為啥。”
滕某家人當(dāng)時(shí)瞞著滕某在醫(yī)院找了心理醫(yī)生,簡(jiǎn)單咨詢后的結(jié)果是“也看不出有啥大問(wèn)題”,之后滕某又恢復(fù)正常上學(xué)。但滕母經(jīng)常聽到滕某說(shuō)“煩得很!煩死了!”滕母說(shuō):“你一個(gè)小孩子,煩什么?”
自此之后滕某性格變得內(nèi)向、膽小,“剪指甲都怕剪到自己。”
第二次自殺,是滕某高一暑假去杭州參加了一個(gè)長(zhǎng)達(dá)40天的美術(shù)魔鬼封閉訓(xùn)練營(yíng)后。
“回來(lái)后一周左右,他又割腕了,一點(diǎn)征兆都沒(méi)有。”這次滕某差點(diǎn)沒(méi)搶救過(guò)來(lái),住院半個(gè)月間滕母一次都沒(méi)敢去看他。“回來(lái)后都不敢跟他說(shuō)話,之后問(wèn)他怎么了,他還是說(shuō)不出原因。”
滕母稱滕某從小喜歡畫畫,一直在學(xué)。由于英語(yǔ)成績(jī)極差,家人想讓滕某找個(gè)專業(yè)方向考大學(xué)。從小學(xué)畫畫的滕某對(duì)自己走美術(shù)這條路“還蠻有信心”。
于是家人高一暑假給滕某報(bào)了上述美術(shù)訓(xùn)練營(yíng),為他藝考做準(zhǔn)備。“但沒(méi)想到回來(lái)后發(fā)生了那種事,自那之后死活再也不愿意畫了。”
自殺后,滕某休學(xué)一個(gè)學(xué)期,滕母每天在家陪他。
家人偷偷通過(guò)網(wǎng)絡(luò)和親戚找了一個(gè)“心理咨詢和教練師”來(lái)治療滕某,這位“持有國(guó)家二級(jí)心理咨詢師證”的治療師見過(guò)滕某兩次,怕他排斥,要通過(guò)對(duì)滕母的治療來(lái)間接影響孩子。他讓滕母自己讀一些“專業(yè)”的書,讓她每天念一些正能量的文字,“每天早晚都要念那些祈禱文,每天要給孩子寫一些想說(shuō)的話,說(shuō)這些可以植入到我的潛意識(shí)里,通過(guò)‘母子連心’來(lái)影響孩子。”滕母回憶說(shuō)。
“當(dāng)時(shí)就差一步就去醫(yī)院找醫(yī)生給他做診斷了。”滕母說(shuō),當(dāng)時(shí)如果滕某再不愿去上學(xué)不出門,就考慮去醫(yī)院找醫(yī)生、給他吃藥。“但一個(gè)學(xué)期后,他又答應(yīng)去上學(xué)了,而且跟同學(xué)相處得挺好,慢慢的好起來(lái)了,緊接著高二高三要高考,就這么稀里糊涂過(guò)來(lái)了。”
休學(xué)的那一學(xué)期,滕某每天窩在家里,白天晚上都拉著窗簾遮光,把自己臥室里所有的抽屜柜子都拉開。“當(dāng)時(shí)就感覺(jué)他是心里面壓抑,又不愿意表露出來(lái)這種感覺(jué)。我們就把他往正面引導(dǎo)。”
休學(xué)結(jié)束后,滕某家人給他換了一所高中繼續(xù)讀書。一切看起來(lái)恢復(fù)正常,只是滕某依然會(huì)說(shuō)“煩死了,煩死了”。家人開導(dǎo)他,“讓他跟性格開朗的孩子在一起”。
“現(xiàn)在回想起來(lái),可能就是因?yàn)楫?dāng)時(shí)表面上看著他去上學(xué)了,恢復(fù)正常了,但是潛在的隱患我們沒(méi)有考慮到。”滕母說(shuō)。
恢復(fù)讀書后的滕某拒絕美術(shù)這條路。有親戚說(shuō)“滕形象還可以”,建議他學(xué)播音主持,但他拒絕了,說(shuō)“唱歌還可以”。于是滕母在別無(wú)選擇的情況下,臨時(shí)又讓他學(xué)唱歌,在白銀給他找了一位聲樂(lè)老師,每周上一次課,之后又去蘭州一所音樂(lè)培訓(xùn)學(xué)校集訓(xùn)半年。
集訓(xùn)后的滕某在2015年初蘭州省聲樂(lè)專業(yè)聯(lián)考中考了全省第91名,當(dāng)時(shí)有5000多人參加。“高考文化課考了365分,英語(yǔ)只考了30多分。但我們已經(jīng)很驕傲了。”滕母說(shuō),“他自己也很滿意。”
送滕某來(lái)成都讀大學(xué)后,一切都讓家里人覺(jué)得“在變好”。滕母每天給滕某發(fā)微信,滕某晚上臨睡前給她回復(fù),告訴她“特別忙,特別充實(shí),每天排練、練琴、參加各種社團(tuán)、學(xué)俄語(yǔ),還買了滑板玩。”“也不是每次都回我。”滕母說(shuō),滕某很少跟她提到朋友同學(xué)的事,話很少,不想說(shuō)的時(shí)候,再怎么問(wèn)也不會(huì)說(shuō)。“跟我說(shuō)宿舍太吵了,我告訴他習(xí)慣了就好,要跟同學(xué)好好相處。”
大一的第一個(gè)寒假,滕某基本呆在家里不出門。說(shuō)“出去沒(méi)啥意思。”家人都覺(jué)得滕某作為男生太安靜、太乖了。“愛看電影,愛看科教頻道,看看探索發(fā)現(xiàn)什么的。”
案發(fā)后,滕某家屬趕到成都,想通過(guò)校方和警方先對(duì)被害人蘆某的家屬表達(dá)歉意。“我們先籌了一部分錢,一兩萬(wàn)塊錢先給他們一些補(bǔ)償。可對(duì)方家長(zhǎng)不愿意見我們。”在成都的幾天,滕某家屬只去做了一次筆錄,被要求簡(jiǎn)單提供孩子以前的情況。
“事情發(fā)生到現(xiàn)在,我們沒(méi)有得到任何消息。只通過(guò)律師知道,警方給孩子做了精神鑒定,說(shuō)一切都要先等結(jié)果。”滕母說(shuō)。
據(jù)此前探針報(bào)道,滕某的父親名叫滕宗武,是甘肅省白銀監(jiān)獄財(cái)務(wù)科副科長(zhǎng)。公開信息顯示,他曾代表監(jiān)獄,多次采購(gòu)心理健康中心功能室設(shè)備項(xiàng)目、圖書及書架等。
“網(wǎng)上有人說(shuō)在監(jiān)獄工作的人培養(yǎng)出來(lái)的孩子,肯定不正常。我們是普通家庭,哪個(gè)家庭想把孩子往殺人干壞事的方向培養(yǎng)。現(xiàn)在是法治社會(huì),該我們承擔(dān)的責(zé)任我們肯定承擔(dān),該孩子承擔(dān)的法律責(zé)任他也一定承擔(dān),他是成年人了。”滕母回應(yīng)已有的報(bào)道說(shuō),“我們肯定盡我們作為家長(zhǎng)的責(zé)任和義務(wù)。我們不是逃避,只是對(duì)方不愿見我們,我們沒(méi)機(jī)會(huì)賠償?shù)狼浮_@是兩個(gè)家庭的悲劇,我們不奢求能被諒解。”
此前被害人蘆某的堂兄蘆海強(qiáng)向記者表示還沒(méi)見到過(guò)滕某家屬,“事發(fā)后不想見他們。”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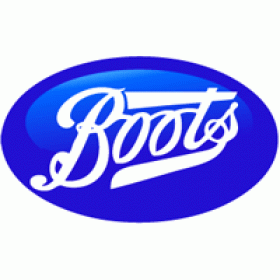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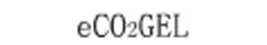
 粵公網(wǎng)安備44030702000122號(hào)
粵公網(wǎng)安備44030702000122號(hào)